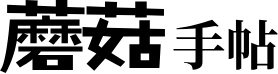文 舒國治
作家
著有《理想的下午》《門外漢的京都》《流浪集》《台北小吃劄記》《窮中談吃》等

最初,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我是準備寫小說的,也寫那種有一點奇詭的散文,從沒想過寫旅行什麼的。寫旅行,幾乎要到了九十年代初。至於寫吃,那已是二十一世紀後的事了。
但這說的是題材。另外很值得講的是風格,也就是,人們會問:「為何你會寫成這樣子?」哪怕你讀海明威,讀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讀張愛玲,讀汪曾祺,皆可以問出同樣的問題。
我現在有一點年歲了,回憶前幾十年,的確可以像旅行(回溯旅程)一樣的講一講諸多因由。五六十年代,我耳中聽到的語言,與看到書報上的用字,已感到自己生活在語言文字不是很豐足的地方。當我自己想要寫東西時,不免想:我該如何行文?我該寫成什麼樣的句子?文句裡涵蘊的是什麼人發出來的聲氣?難不成發出像徐志摩的聲氣?不可能,他太輕快靈動了。也不可能發出像魯迅的聲氣,他太憤怒了。
我雖沒想太多,也不可能思辨得太完備,但已知我要寫我忍受得了的文句,更確知我要寫我認同的題材。
先別說及大方向(如題材、如內容、如風格、如主題……),只說文字。所謂文字,單說開頭第一句話:「小明早上起床,……」要怎麼將第一二十個字寫下來,接著又是幾十字,再又幾十字,這些「一定要被寫下來」的字,如何受你選上、受你推展,最後令你看了有生趣,令讀者看了有魅力,停都停不下來,便是寫作極要緊的事體。
哪怕還沒有故事,哪怕還沒有主題,人也可以一句一句的往下寫,照樣寫成有節奏有起伏的一些句子、一些段章。「街角停了一輛車已經好幾天了。鄰居經過會開始議論,或許是引擎蓋上的落葉堆得已厚,或許是車頂的鳥糞已白漬斑斑。我們家也注意到了。爺爺每天早上推開四樓的窗,總會往下瞧一眼這輛車……」我隨便舉這例子,不過想點出有些文字是不自禁推向「故事」的,如上例,而不是純散文字句。倘若你不想推展故事,只想使讀者專注讀文字、讀句段,且很有趣味,則行文不可太平,甚至不可太緩。另外,美文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自認我從來沒想過要寫美文,因為「美」可以由許多別的雜類、平淡、簡單的東西,最後結成的,而不必是「作美」出來的。就像我從不追求「美食」一樣。許多好吃的東西,在於它真實、平簡與耐心烹燒,最後就美了。但它的模樣,或它的氣勢,從來不是「美食」的意指。也完全不需要是。
文章亦然。完全不需寫成美文,亦可以是經由質樸、平淡、琢磨,成為一篇好文章。
所以說,人的氣質,形成人的文章之格調。
至於我寫東西有點文白夾雜這一節。白話是很難的。白話要說得又看似平易、卻又漂亮、又其實很簡鍊,則是需要打造的。而這種打造,需要很多人不斷的在說話中逐漸的演化它。也就是說各省各區的人都湊到了一塊大城市,然後將官話一起說得很清暢、很流利,便或就成了。然而五、六十年前的台灣各市鎮,大夥還沒把話講成很圓熟,已然有人等不及必須寫劇本、必須做文章了。於是寫出來的文章,我左看右看,總覺得不順眼。若我自己將來寫東西,看來別寫成那樣為宜。又中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了幾篇文言文,似懂非懂,但覺運用得妙,也會是有神采的文字。
另外,文言文有一種古人式的距離感,寫在筆下,有時產生一股遠處誨人的尊嚴語氣,往往自然而然教讀者生出服氣之閱讀情懷。甚至省了讀者想要與你辯論的心思。
再說讀書。太多的書我沒法看,便是題材吸引不了我,往往其文字也吸引不了我。要知道,題材與文字常是息息相關的。有一本書,叫《未央歌》,講抗戰時大學生在大後方的故事,四五十年前極受歡迎,一直到現在仍有人讀,但我一讀開頭,便讀不下去了。
顯然,我讀東西不甚寬容。在書店任意翻看時,常帶著一絲「瞧不起」的冷眼。尤其當年太多溫吞水似的內容與溫吞水似的寫者常會隨手翻到。
當時的社會也不行。或者說,年輕時放眼看你的周遭,什麼皆不行。正因為有那樣的爛周遭,才撥動你想要講髒話或寫作的動機,不是嗎?
不太讀得下去,也在於我年少時的閱讀習慣沒有建立。高中畢業前,我原不是文藝少年。還比較算是武藝少年,喜歡打球、戶外遠遠勝於看書。
那時公教人員寫的東西,有一種他們的「謹於此、慎於彼」的習味。就像有些在銀行上班,公餘寫作,寫出來的就有一股飯碗已打理好於是可以放心寫東西的氣質。
他們中有的人其實寫得很用深心,但他們發文的起因終究不是我們所謂的「有意思」。
可見人生的定調,真的是一樁很不容易之事。太多人一寫,寫著寫著就寫成他日後的一生。他定調定得太四平八穩,終於連寫東西也寫成四平八穩體矣。
小說的推演,常在於寫作者他早年是怎麼獲知小說的。亦即:他是怎麼從看小說當中逐漸發展出自己蘊想小說的習慣與能力。我幼時看小說不那麼多,主要戶外遊戲與球類取代了看書;故而開始想寫小說時,自知不敢往傳統舊俄的巨著去學模樣,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太龐雜浩繁了。也不見得對簡·奧斯丁、福樓拜等大家有所心得。後來稍翻德國的湯瑪斯·曼,覺得太把框架弄成宏偉,毫無自然興發的熱情,這樣的書倘有人臣服,會害了他太想把事情做成有形有樣,很容易害後學者變成虛有其表。就像常常把「大河小說」放在心上的作家,很容易著了「偉大」的道。
若說要寫成極具個人風格,例如像芥川龍之介,那又非得把自己設身處境弄成芥川的幽微極矣的那種不世出的狀態,看來不是人人可以仿習的。更別講國情之不同、時代之不同、與每人秉性之不同了。莫泊桑的故事如此豐多,也不是說學就學得來的。
偵探小說、科幻小說,在七十年代也已有了一點,只是我沒去探索。
至於武俠小說這一類別,我做為四年級生(五十年代出生),一來已是baby boomer(戰後嬰兒潮)一員,離亂之苦未受,不易寫大恨大愛跌宕起伏的武俠;二來六十年代青春活力薰陶、西洋娛樂浸潤,已積累另一股「高蹈」之念,未必將武俠小說看在眼裏。更別提人受西方雜項牽引,中國古東西不得專注,武俠寫作或也力有未逮。
主要的心念,還是繫於「藝術感」很重的短篇小說。然又未必知道怎麼去構思。有時只能從字句開始;寫它個幾行字,寫一些開頭,寫一些沒頭沒尾的中段。然後想,這些筆記,將來會變成小說嗎?
同時也寫些散文。不知怎的,我很早就注意所謂「文體」這件事了。一篇東西,常因它的文體,得到你眼神之停留。好的文體家,極有可能他的太多篇東西都令讀者印象深刻,有時這還不是學來的,是他與生俱來的某種創作基因也不一定。
今日,我的職業雖算是作家,但這也是近十多年才成形的事。原先的幾十年,我沒設計自己的路為寫作。有很長的歲月,我不確定要做何種工作。
每個人有每個人適合做的事,但最好做那得以發揚自身十足能耐的工作。我若每天伏案寫作,不做他事,我自己覺得太可惜了。為什麼?因為我愛玩,愛一天中大多時間在外頭活動,找朋友,找風景,找有意思的東西看(但甚少是書),帶動社會的聯繫,然後,偶爾寫上一點東西糊口,也便成了。
簡略的講一下自己寫東西的經過,豈不也像是講一段旅行中的途程?
2013-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