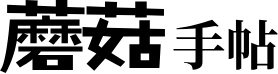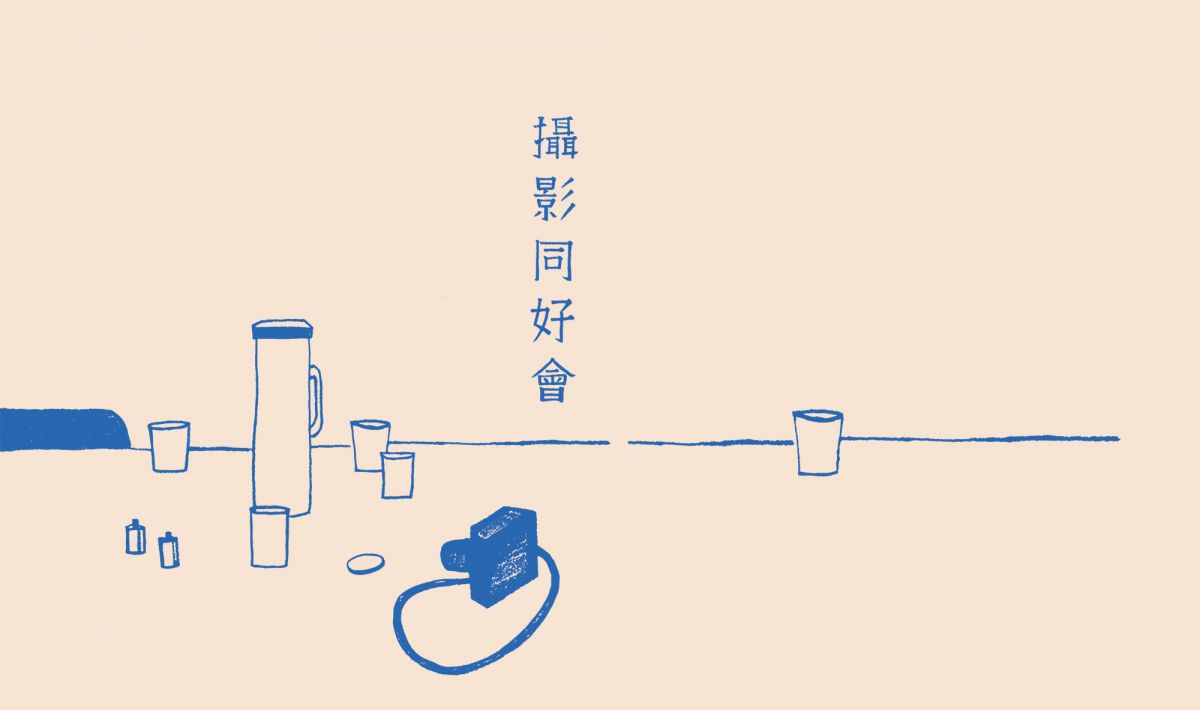文 吳松明
攝影 吳松明 曾弘煒 夏紹虞
插畫 湯姆
不久前,我跟大學同窗阿虞到戲院看一部由他執鏡的電影,這是我第一次坐在大螢幕前看著他拍攝的電影。電影放映結束後,導演和幾個工作人員上台和觀眾交換意見,看著他站在台上說話的樣子,自然地想起第一次看到他上台和觀眾討論他的電影時的學生模樣。無論如何,去看電影前後,心裡充滿一種奇妙的變化而愉快的感覺。
雖然我沒有機會看到阿虞在拍片現場工作的樣子,不過每次他籌錢拍完自己編導的短篇電影或者動畫,我們總是有機會坐在小螢幕前一起觀賞說笑,那時腦海裡和著在美術系同窗四年一起玩耍的時光,心裡總是感到愉快。若是回想他拍片這件事可以做到現在,那麼我當然記得大三那年就常聽他說想要拍電影了。
我那時候還不太清楚阿虞拿相機在拍什麼,只記得偶而看到他秀出在暗房沖洗的黑白照片,或是將幻燈片彩繪,讓我們置身在那奇怪調調的投影當中。他開始迷戀電影以後,就不怎麼愛去教室畫畫,不過,這些現象在美術系的學生當中也不算特別。我本來以為他想要當畫家,卻常看到他在隨身畫簿裡寫著密密麻麻的東西,塗滿了像電影分鏡式的圖畫。當我第一次看到他拿著一台16釐米的攝影機在手上比劃的模樣,突然聽到攝影機的發條輕脆地轉動聲,那真是令人驚訝!他果然用那台借來的攝影機拍了一部實驗短片,而且在畢業前夕忙著對外公開發表。
關於那部短片,我只知道那個暑假他不見人影地忙著跟嘉行、煒煒和阿達一起拍攝和剪接。影片發表以後,我只看過一次,是他帶拷貝片回到巫雲山莊放映。我們擠在他那間牆壁漆黑的房間裡,圍著一台老舊而不太靈光的電視機,暗黑之中,每張凝注在螢幕裡的臉上閃爍著有聲響的光影,那個驚奇的觀看情景總是留在我的記憶裡。至於影片的內容,我已經不那麼清楚了,但是我還記得片尾的配樂響起The Sex Pistols翻唱那首《My Way》時,他們正騎著野狼125的摩托車在茫茫的西濱公路上奔馳前進。
大概七、八年前開始,我的朋友紛紛拿著數位相機和數位攝影機在我眼前晃來晃去時,我也免不了花錢都買來嚐試一番。有一段時間裡,我花時間坐在電腦螢幕前學著處理影像,存在電腦裡的數位影像突然之間開始進進出出,看起來似乎跟生活在不同距離的朋友有了聯繫。只是,使用數位相機的新鮮感並沒有持續太久,我終究不太喜歡數位影像的色調和質感,還是放棄我的數位相機。
每次經過相機店,看到醒目誘人的各家廠牌的新機種擺在櫥窗內,我也漸漸覺得沒有跟進升級似乎也不會構成困擾了。不過,數位相機的功能進化愈來愈厲害時,我反而想起我的第一台相機Nikon F501的存在,雖然那台自動對焦的相機在我讀大一時好不容易買來,卻不常使用而遭閒置。我將發霉的鏡頭拿去整理一番,裝上底片還是可以拍照。然後,為了將新舊底片數位化,掃描底片變成一種趣味,如此,才能找到一些自己感到愉快的照片寄給朋友!

我很晚才感到有拍照的需要,那是因為看到我的圖畫作品愈來愈多,卻不能一直請攝影師拍照,我因此才學會使用相機翻拍自己的作品。我也很訝異,原來我從未理解過那台單眼相機的性能,所以一直被當成傻瓜相機使用,難怪當學生該會拍作品的事也沒學好。我接著興起了拍照的興趣,這樣不至於讓我整天不出門,有時反而覺得是相機帶我出去透氣,這對我獨自在家畫圖的工作型態變的很重要。尤其在景氣低落的期間,看著許多忙碌在外的人,我的工作顯的微不足道,然而,拍照這件事,至少可以使我跟外面保持親近。
剛開始那段時間,我似乎不計成本地消耗許多底片,況且每天不只買一包菸抽,情況漸漸讓我感到為難,結果卻沒想到結果這讓我在一夜之間終止抽菸這個長久的習慣。沒幾年的時間,那些由買菸錢換來的幻燈片堆積愈來愈多了。有時自己沒節制地按下快門,聽到輕脆的聲音,偶而還會想起從前用食指彈去菸灰的樣子,不過,跟朋友一起吸菸吐氣感覺像是久遠以前的事了。
現在我還是喜歡用機械式的相機拍照,雖然屬於這些相機的時代早已遠離,但是當我拿來一直拍著生活動線裡的風景,或重複拍著熟面孔時,每個零件依然工作的很好。至於拍照的單純理由,我想過,至少可以為我的圖畫好好拍一張照片,也可以對著我想要多看一眼的光景按下快門。此外,當我覺得腦海裡的過去愈來愈模糊時,就愈想將眼前的現在紀錄的更清楚,所以不知不覺就用到了大片幅的底片。

嘉行和煒煒畢業後就成立工作室,一邊接案子,一邊做自己的影像。他們一直都在同個地方做各自的事,那工作室名稱就以學生時代一起拍片時取的「寶大J」開始,而我也開始在家畫畫這件事。畢業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們在各自的角落裡忙,偶而才有碰面聚會,所以在我的相簿裡,有關他們的工作室照片,在我還沒有拍照的習慣之前,實在是沒拍過幾張。他們的照片開始增多,可能是他們的新工作室搬到捷運站附近以後,我常順路去那裡的緣故。
習慣了拿底片去沖洗以後,使我常在傍晚時分暫時離開北投住所,他們的辦公室似乎成了我來回市區途中的歇腳處。我總是習慣在雙連站下車,然後慢慢走去他們的辦公室,常常只是喝一杯咖啡的時間,跟老朋友聊幾句話,偶而也隨手拍幾張照才離開。我若不是從那裡走去轉搭公車到東區的相館,不然就是往圓環走去,或繞過延平北路穿過北門到博愛路的相館。可是我怎麼老是在同樣的路上漫走,只為了等待底片經過時間和藥水的化學變化所產生的影像結果?
有一陣子,他們的辦公室也流行用底片拍照,我知道他們除了日常的工作,每隔一段時間,若是看到個個都要開始為即將出刊的手帖負責採訪、寫稿和拍照,或是得為他們的新產品上鏡頭,那麼我知道該是快換季的時候了。他們紛紛把老相機拿出來玩耍,也許想試著在那本小季刊裡重用有底片味道的圖片?嘉行也把家裡的老相機找出來,當他拿出一台銀色的Nikon FM2亮在我眼前,對於他那台學生時代的相機,我幾乎沒有印象。後來他漸漸有底片要沖洗,若在傍晚快下班時分有順路,偶而會跟我一起邊走邊聊地去博愛路的相館。
雖然以前拍的照片不多,現在看來每張都覺得可貴!這些跟老朋友有關的照片,玫君出現的機會還不少。那時她在木柵唸書,可是我們覺得她對電影和新潮的音樂很內行,大概在煒煒和嘉行常上台北找阿虞合作拍片以後,她就比較常跟我們一起玩耍。在偶然的聚會裡,她常微笑著出現,有時她安靜的像一面鏡子,即使話不多,每次也都感到愉快。有一段時間,因為常去有電影的場所和可以聽音樂跳舞的酒吧玩,這使我們看起來不像是美術系的學生,而她似乎也不像來自中文系。我們同年畢業,她暫時在一家進口新潮音樂的唱片行工作,即使後來她遠嫁到澳洲,在彼此偶然的聯繫裡,有關電影和搖滾音樂的訊息總是少不了。



每次她回到台灣跟我們碰面,或是偶而接到她從南半球打來的電話,除了感到高興之外,還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時空距離感。像是前幾年,我要搬離新北投那間住了很多年的住所前夕,看見她和她的先生突然出現在我的門口時的驚喜,或是今年再見到他們回來也是如此。尤其她的身體才剛從去年突來的一場病痛中康復,他們長途開車到台東與我們會合,感覺像似穿越時空來到我的面前。
這一兩年,我還在為住所搬遷煩惱時,有幾年不在台灣的阿虞也回到台北繼續拍片,而嘉行已經和朋友合夥去台東蓋個夢想屋,那條縱貫花東的台9線已經成了他和家人暫時遠離台北的動線。然而,聽到有關那裡的描述更具體時,愈讓人感到好奇,所以今年初,玫君和她的先生從澳洲回到台灣,那間遠方的小木屋就成了大家都想去的地方。
那間小木屋單獨蓋在山腳下,在一條深長小徑盡頭的椰子林裡。在那十幾坪的雙層小屋,我們待了幾個白天和夜晚,一起吃飯,一起移動外出,也一起睡在像登山屋的通舖裡。屋裡沒有電視,也沒有電話網路,桌上除了幾把偶有聲響的手機,還有聽不完的音樂,相機和底片也擺滿桌。我們隨手到處拍照的樣子,看起來像一群外拍的攝影同好會,這是從前沒有過的景象。大家坐在一塊,看著彷彿從前一起玩耍的熟悉模樣,即使沒多說什麼話,也感到愉快。
時間過的像車窗外迅速消失的風景,帶來的音樂都聽完了,底片都拍完了,那麼,我們也將要像椰子樹的葉子那樣分開。

回台北的途中,我還是跟煒煒坐在阿虞他們的車上。車內除了長途的衛星導航指示聲,煒煒放的音樂很好聽,即使重複再聽,我也不知道那是誰的音樂,這個從他學生時代到現在沒有稍減的興趣,我沒跟上已經很久了,顯然我只能當聽眾。或許現在少了以前一起抽菸聊音樂的樂趣,但也漸漸有機會看到阿虞拿相機在拍什麼,聽煒煒說要把學生時代買的那台Nikon F3拿出來重新整理使用,已經不只一次了,那麼,我們還會想到一起拍照這回事?
車子在陽光中的濱海公路上加速前進,偶有成群的年輕人騎摩托車出現在窗外,當我瞇起眼睛望著,似乎看到一條長長的海平線將每個不同距離的身影連繫牽引在一起,即使坐在車內,那讓我想起大學畢業前夕我們一起騎摩托車在濱海公路上來回奔馳的身影,彷彿在車窗外,而海風迎面吹拂的感覺似乎還留在臉上。然而,前方沿著海岸的路途多彎曲,無論如何,當我回頭望向大海,那條遠方的海平線始終平穩地畫在車窗外。
2011-09-01